歌手易扬个人资料 模特易扬个人资料
◎易扬
出名趁早的周嘉宁,绝对算得上是一位年轻的老作家了。早在23年前,她就因新概念作文大赛一战成名,不仅19岁就出版了小说处女作,更是在之后5年多时间里接连捧出了4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如此“高产”几乎堪比事业巅峰期的歌手张信哲。不过,最近几年,周嘉宁明显慢了下来,她一边在活动中自省“之前很多书都是不应该出版的”,一边把更多时间放在了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西方文学翻译上。在这本新作《浪的景观》之前,周嘉宁也已经4年没有出版小说单行本了。
青春
以青春文学出道和成名,“青春作家”自然也成了周嘉宁最为脍炙人口的身份标签。从滥觞之日起,“青春写作”就时常沦陷于各种睥睨,也很少以正面褒义的形象出现,就连因为小说主人公多为青春期少年而数次“躺枪”的路内,都不得不委屈地吐槽“青春小说是个侮辱性的用词”。在周嘉宁201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密林中》中,封底显眼位置印着作家孙甘露的一句推荐:“《密林中》是周嘉宁对青春写作彻底的告别。”撇开小说文本,我们当然还可以读出另外一层意思:对所谓的“青春文学”,不仅仅年轻作家本人避之不及,作为旁观者的严肃作家更是高看不上,是否进行青春写作,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他们评判年轻作家成熟与否、作品优劣的标尺。
然而,“青春写作”于周嘉宁而言,就有如生命“脐带”,她二十余年的创作营养来自于此,所谓糟粕也由此输出,具体到某时某刻,“脐带”不可或缺,待到水到渠成,也必会自然脱落。《浪的景观》虽然仍会留着诸如以单字命名人物姓名这样独特的青春文学“胎记”,但小说情感的喷薄则显得更为冷静和节制。值得一提的是,显然认识到青春文学在情感把控上的弊端,并且更为注重对人物喜怒哀乐的收敛,但周嘉宁并没有一味地将人物情感张弛的洞孔堵死,在《再见日食》里,拓看到新闻中飞机撞击双子楼腾起的巨大烟雾时,便觉得泉也身在其中,伤感得“泪流不止”;在同名中篇《浪的景观》中,抢到首批货物的“我”激动到“鼻涕眼泪横流”,“一说话却呼呼流出更多眼泪”;而在另一篇《明日派对》里,站在礁滩上的“我”和王鹿,见证着心境的变更,感觉自己在黑暗中“很快被迅速涨起来的潮水逼得节节败退”。周嘉宁让这些偶有爆发的显性情感,与她善于通过比喻和意象所创造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外在成像碰撞交融在一起,并在小说内部形成了具有独特张力的化学反应。
与此同时,《浪的景观》中的三则故事,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将主人公们纷纷“圈禁”在孤独孤僻的个体情感之中,而是带领他们走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在拓和泉、“我”和潇潇、王鹿和京这些似是而非的爱情之中,周嘉宁所要透视的当然已不再是爱情本身,更是这些爱情所身处的时代和社会,是这些爱情究竟因何变得异常艰难或是无疾而终。
时代
收录在《浪的景观》里的三部中篇,创作时间横亘四年,贯穿《再见日食》《浪的景观》《明日派对》,有一条自始至终的明线,用评论家金理的话来说,就是“向一个混乱无序又生机勃勃、边角毛茸茸还未被修剪平整的时代致敬”。从这个意义上讲,《浪的景观》既可以看成是独立文本的合辑,更可以当作是一气呵成的整体。
“时间”是周嘉宁特别关注的小说元素,在《浪的景观》里,诸如2000年这样具体的年份,以及“911”恐怖袭击、北京申奥成功、上海华亭路市场拆迁这些发生于千禧年前后的具体事件,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凸显和强化着。除此之外,书中还有不少具有鲜明时代性特征的独特意象,它们打破篇目边界,反复分布在各个文本之中,既成为不同小说人物的共有记忆,也成为不同故事情节的共同背景。比如,三部小说都提到了那些影响一代人的明星歌手,在《明日派对》中,周嘉宁更是让罗大佑走入故事情节,来到“我”和王鹿身边,成为小说中一名“真实的虚构人物”。又比如,《浪的景观》和《明日派对》都写到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席卷而来的层层浪潮中,每个个体都无法置身事外,这其中既然有《明日派对》里前路已被水泥封死、此船无法远行的无奈,当然也就会有《浪的景观》中乘势而上、暂居浪尖的快感。
周嘉宁写到了很多落空的情感、消逝的景象和从未现身的人物。《再见日食》里的泉贯穿着整部小说,《明日派对》里的张宙导引着故事发展,可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但无论是泉还是张宙,他们都只活跃于周边人的评价和回忆、信件和照片、磁带和影像之中,仿佛虚无缥缈,但又真实存在。《再见日食》的叙事频繁往返于过去和现在,温柔而碎心,但如同一段不再的青春情愫,泉已经和所有人都彻底失联了;《明日派对》的情节流转于上海、南京等各个地方,哪里都曾活跃着张宙的传说,但他却决意和当下告别,离开最熟悉的圈子,前往情有独钟的边境。在对过去时光深深的眷恋之中,周嘉宁所展示的是记忆的断层和经历的裂痕,它们跟随那个远去的时代一起,被折叠封存后压入箱底,就好像是《浪的景观》里那颗撞断的牙齿又被重新补上完好如初一样,待到海不扬波,过往的经历就仿佛真的未曾存在,并固化成为另一种新的风景。
她们
周嘉宁的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笔下的人物伴随着作家本人的成长,也同样处在动态成长的过程之中。在2006年出版的《往南方岁月去》中,主人公“我”的身份是大学生和职场新人;2015年创作的《密林中》仍然从主人公的大学生涯开启故事,但情节的跨度已经到了10年后的30岁;2019年的《再见日食》中,蒂娜和泉保守估算都得有40岁了。周嘉宁一边塑造着与自己近乎同龄的女性形象,一边也是审视着当下的自我处境,并以一种付托于小说的方式,让真实的心境在虚构的人物身上得到刻录和留存。
周嘉宁是个女性定位很强的写作者,女性基本上占据了其小说主人公的整个谱系;就连她多次译介的珍妮特·温特森、弗兰纳里·奥康纳等人,虽然写作风格不尽相同,但也无一不是女性。值得注意的是,从最初的小说创作开始,周嘉宁笔下的女性主角就都附着着离群叛逆的因子,正如《密林中》在开篇就写道“阳阳从一开始就是没有名字的配角”一样,沉溺于爱情之中。周嘉宁笔下的女性更多时候都处于失势的状态和被支配的地位,但渴望独立的意识也未曾不在她们身上萌生过发芽过。所谓“叛逆”,某种程度上正是她们试图摆脱女性身份束缚,闯入另外一个全新世界和话语体系的姿态。
在最新创作的《再见日食》《浪的景观》中,周嘉宁一反常态,破天荒地将小说主人公们设置成了男性,前者里的“拓”多愁善感,多少还有点阴柔气质,后者中的“我”敢冲敢闯,完全就是个阳刚的拼命三郎。不同于20世纪末徐坤等先锋作家以“性别置换”抗衡男性话语权,周嘉宁所要做的或许更是以去性别化的写作来冲淡“女性写作”这个多少有些别扭的分类,并以创作的探索践行起伍尔夫“雌雄同体”的理论——“任何纯粹的、单一的男性或者女性,都是致命的……任何创造性的行为,都是必须有男性和女性之间心灵的某种协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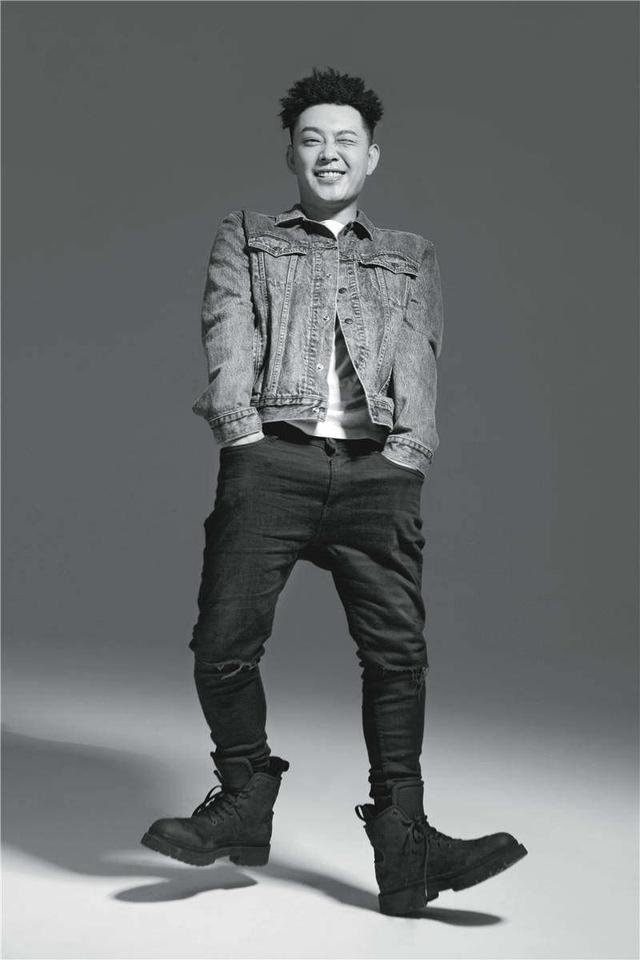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