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黄雯个人资料 中国内地女演员 黄雯
黄雯:冠中老师,我是黄雯,是负责这期《0086》的特约记者,许久没见了。知道您前阵子一直在北京和香港之间来回奔波,作为一个长住北京的著名国际文化人,现在的兴趣点怎么又转回到了自己幼年生长的地方?是因为距离感造成的吗?顺便聊聊您最近在忙些什么?又有什么新的打算和计划?
陈冠中:我不算国际文化人,大不了是在两岸三地都住过的文化人。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就不曾在香港工作,主要在北京,也有六年在台北。在北京呆着写作是我现在的总规划。另外,我当了公民社会组织国际绿色和平的董事,算是比较忙的正事。
黄雯:这期杂志的主题是《中国发现中国》,作为香港《号外》杂志的创始人,这些年来您跨越了诸多行业,从事作家、电影、媒体策划、娱乐产业经营等等。您的这种文化跨界的特殊性,以及您的国际化身份,一定使您对中国文化有着特殊的体验和感情。想听听这一年来,针对中国的文化事件,哪些给您带来比较大的刺激,哪些又让您不以为然?很想听听您独特的感受。
陈冠中: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规模远超过港台,充满变幻的特殊性,参考港台经验的日子显然已经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革发展自己这个潜力超大却成绩未尽理想的市场。
08年中国事多,都有改变人心的文化含义,譬如:这次奥运后中国人大概很少再会拿东亚病夫来说事,结束了一个百年情结;汶川地震,启发了很多人去当志愿工作者以及成立公民社会组织;更多农地流转农民进城;食品安全意识提升;大家上了金融股票地产的一课等等。我认为08年是国人心态演变、经验更新很重要的一年,而今年的社会事件的文化影响远超过个别文化事件。
黄雯:作为一个研究东西方文化的人士,您怎样看待西方文化对中国现状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的发展是更多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陈冠中:今天的中国不是一个世纪前的中国,一个在1908年被急冻的中国人若在今天复活,会觉得今日中国非常陌生但又带点熟悉。康德曾问:历史有真的进步吗?他回答说不好证明,但还是有的。我觉得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就是例子。我相信绝大部份人细想之下都不愿意回到1908年,而每一个在看这篇访谈的人也都是现代化的利益共享者。西方文化影响中国是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早就是中外文化的深层混合体。不是只有“前现代”的传统文化才算是中国文化,由晚清、民国到49年至今的当代文化都已经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一切有助于形成当代中国主体性的文化都是今天的中国文化。近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制订国际共同发展规则上将扮演重要角色,中外交往应会更加繁密,现在要问的是:一、如何促进开放交流和混合创新,让世界各地包括西方文化继续进来,同时让我们的文化出去,增加相互理解,共同营造和谐世界;二、如何保持我们的主体性、保育我们的差异性、滋润我们文化的特色,让外来文化为我所用。我认为中国现在越来越有能力同时吸收外来文化、输出本土文化,并强化自己的主体性。
黄雯:中国今年发生了许多事件,比如申奥路途的艰辛、抵制家乐福事件等等,引起了“爱国人士”同“自由主义者”之间热火朝天的争执,到了后期,上升成了国内精英阶层同草根之间的观念对峙,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矛盾的?在这种矛盾面前,您是个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是否也同您特殊身份有关联?
陈冠中:我接触到的国人几乎都爱国,但立场可以很不相同。现在很多的争执都是跟“稻草人”的争执:先替假想对手贴一个群体性的标签,然后把对手描述得愚蠢无比而且道德可疑,然后攻击这个愚蠢的对手,当然大获全胜,占尽道德或修辞的制高点。但这只是在攻击你自己制造出来的稻草人,现实里的爱国人士、自由主义者、精英、草根都不是只有一种人或一个声音,也不见得必然是对立。真实里每一个人都会有判断失误的时候,但都比对手想象中更高明。我以自己唯一擅长的方式参与国是:写我的文章。
黄雯:记得您曾经接受一个采访,意思是说,香港的文化中有许多传统中国的元素,比如重视国学等等,而来到大陆之后,发现大陆这边反倒失去许多传统的东西,对国学不够重视,所以才产生国学通俗演绎家于丹火爆的现象。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能否深刻阐释一下?
陈冠中:英国式殖民地的其中一种模式是相对放任让当地社会文化自生自灭,加上殖民地香港没有受到上世纪初大陆五四新文化的正面冲击,也没有经历上世纪中叶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大力清洗,结果很吊诡的反而保留了一部份在大陆已被遮蔽的传统中国文化。五十到七十年代香港中小学生在学校上中文课都会读到中国经典包括多篇论语,同期的大陆学生却没有或只作批判对象。
黄雯:这种现象是否也说明是一种大国的自信呢?也就是“根基”的东西,本身就存在这个民族身体里了,已经不需要再继续强调了。可在香港不同,因为全盘西化教育的香港,是不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抓住“救命稻草”的感觉?有点象日本人那种岛国心理相似。不好意思,这个比喻可能不恰当。
陈冠中:问题不是这样的。再自信的大国也不可能不去叫下一代学习自己的既有经典文化。可以说,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才是令人费解的有意识的动用国家力量推动“全盘西化”的教育。殖民地香港的情况其实较简单也很好理解,社会里的大量传统中国成份,只是自然遗留下来的生活方式,香港人没那么有使命情结。虽然学校要大家学中文,很多人觉得英文吃得开,还是不肯好好去学中文,纯是功利考虑,但话说回来,就算在殖民地时代,也有不少家长坚持把子女送去着重中文教育的学校。
黄雯:中国现在一边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提高全民素质;一边对外开放,承担在国际上重要的角色。您觉着中国元素在目前的中国文化中是正在消减,还是增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局面?假如是消减,乐观的说,是否是一种文化“曲线救国”的必经阶段?
陈冠中:文化从来不是纯粹的,现阶段的文化是上一阶段混杂的成果。现在“最中国”的元素如青花原来自西域。问题只是混哪些外来文化和如何混法。任何有活力的文化都是要不断吸取外来文化以求创新,重点是要同时保持甚至强化自己的主体性,即文化上的自主创新。大家要懂得拒绝文化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才顾名思义不需要创新,故也不需要新的文化元素。文化发展不是零和游戏,不是依非此即彼的逻辑而是更像毛虫蜕变为蝴蝶。文化与经济发展也不是对立的,譬如传统中国文化讲究的诚信,恰是现在市场经济健全发展的关键元素。我的感觉是,因为整体国力增强、生活改善,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比过去三十年更旺盛,外来文化、传统文化的元素皆在增加,投进来的、挖出来的,都可以变成我们的新养份,为我所用。
黄雯:您是怎样看待张艺谋导演的那场奥运大秀?从审美到理念的传达,很明显的带着中国元素,既要表现国际化,又要体现民族感,这种传达对我来说是相当成功的。您是怎么看待这种传达的?
陈冠中:趁奥运集中世人目光的机会,一举大手笔推出华丽如汉赋的中国总体形象,这种传达是成功的。
黄雯:您认为“中国特色”应该怎样表达,才更容易在国际上被认同和接受?是用西方的形式来阐释东方的内容?还是保留东方人的神秘特性,自然吸引西方人自动来融入?
陈冠中:两者都不是,两者恰都是东方主义。大家应该很有自信的认为,当前的中国特色己超越了东方西方的二分法,不再是非此即彼,而是融合古今中外各方文明的新品种。这个新品种虽是混杂的品种却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已成了我们的新传统、新主体。当然,我们首先应是为了自己而不是别人而创造文化,其它人将学习借鉴我们的范畴和问题意识来阐释我们的文化。
黄雯:比如在日本或韩国,我认为这两个相邻中国的国家,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方面就做的非常好。他们在发展自身建设同时,很谨慎地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方面对发展中的中国是否该有些良性的借鉴?如何借鉴?
陈冠中:我对日本不算熟悉,大抵感觉它保护自己文化传统的意识确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强,但日本早就是发达国家,不过传统文化也要在明治西化国力增强后,才反弹回潮,我想这与国家富裕不无关系。原是外来的唐文化和佛教文化在日本及宋明文化在韩国,都不论源头的被视为当地文化的态度,也值得借鉴。当然有时候外国人也把日本浪漫化了。譬如上世纪将日本禅文化推到全世界最得力的铃木大拙,他那版本的日本禅混杂了当时西方本身的一些另类观念,一片和谐、宁静、唯美、超脱,深合当代个人主义式的性灵胃口,诱发了世人对当代日本文化的新想象,其实铃本所建构的日本禅文化,跟当年真正的日本禅教不完全是一回事,遮蔽了日本禅的激烈宗派性、严刻纪律性、对世俗权力的依附性,且不说对军国主义的支持。
黄雯:记得多年前看过您写过的一本长篇小说《什么都没发生》,作为一个做过许多“文化实事”的跨界人士,居然有着敏感细腻的笔触,很纯文学的描述了一个“浪子”的生存态。当时对男主人公的虚无感的体现,影响非常深刻。是否在您多重身份的演绎下,有着挺沉重的漂泊感?您作为一个国际多元化人士,是否隐藏着一种缺少根基的感觉?您也说过时常忙得没法写小说了,那么文学是否是您内心的一种隐痛,或者说是一种“寻根”的失落感而触发的文学创作冲动?
陈冠中:小说所承载的,确不是其它文体所能替代。在古希腊,悲剧作家与哲学家常互相竞争,看谁更能洞悉世情,结果是各胜擅场。小说能处理人生暧昧和人性矛盾,当代中国充满着暧昧与矛盾,有时候好像只能用小说去表达。我一直还想写这样的小说。很多创作都可能跟创作者的“寻”和心理欠缺有关,但不一定是狭义的寻根。
黄雯:您认为中国还有哪些有价值的东西没被世人发现?
陈冠中:中国的养身保健之术,在华人圈以外虽已渐为世人所知,但远远未够普及。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模式,亦值得有人做深入研究。世人也应该多理解一点孔孟老庄。
黄雯:如果由您向世界推荐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东西,您推荐什么?
陈冠中:中国养生保健之术。
黄雯:看您对城市建筑方面,有着很多独特的见解,你能评出在中国“最中国”的城市是哪座?
陈冠中:不能,因为我不懂什么叫最中国的城市。中国本身是个复杂混合体。前现代中国城市最发达是在元代、清代这两个所谓外族统治的朝代,包括北京这样的政治城市及江南的市场性市民城市。今天,仅存的“原生态”前现代中国城镇都在申报世界遗产或以活人博物馆形式搞旅游,这当然有价值,但若说它们代表中国就没有当代意义。不过,如果说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些大面积迁拆后重建的崭新城市,你也会觉得不是味道。当代城市虽然受全球化影响程度不一,文化上都是混杂的,而且都受了不同年代的现代规划理念影响,不宜用“最中国”这样的概念去套。还是看看谁宜居、谁宜经济发展、谁规划得好、谁把历史保育得好吧。
黄雯:“中国发现中国”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发现自信,一个民族的自信。有了这种自信,一时期的文化符号被遮蔽和隐藏,并不说明什么。长期的自信才能造就一个不怕被抹杀的未来,这种民族的自豪感有时候还是挺重要的。这一年的许多变化,让我从一个“自由派”几乎成长成了中国的“新左派”。对您来说,“中国发现中国”最重要的是发现什么?为什么是它?
陈冠中:一个民族是要有自信和自豪感。我曾写过每个地方都要发展自己的问题意识、学自己的历史、总结自己的经验并以自己作为方法,就是要有主体意识,这大概也是中国发现中国的意思。不过我们要小心语言思维的“本质主义”谬误,不要把把复数的中国文化单一化,把多文化的民族变成单文化,把中国文化主体性和自主创新误理解为排斥外来文化。今天的中国人没道理不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但也没道理不去承认和克服各种国族缺点。我们要发现的是我们的平常心,学会不再仰视或俯视而是平视自己的文化和外来文化,我理解这才是文化自信的表现。细究下来,我们知道自由主义者的大部份政治主张都是要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的,所以自由主义与国家没有必然矛盾。真正的新左派既应是支持弱势群体也应是国际主义者。近年许多人变成沙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他们更多是向反启蒙理性的新保守主义倾斜。
黄雯:最后一个问题,对于2009年的到来,您有什么期待吗?有什么良好的心愿期望实现?比如又要远足去另外一座城市旅行等等?
陈冠中:明年初打算去甘肃的定西和陇东一带走走。良好的心愿是大家更有平常心、执政者多做好事、中国变得更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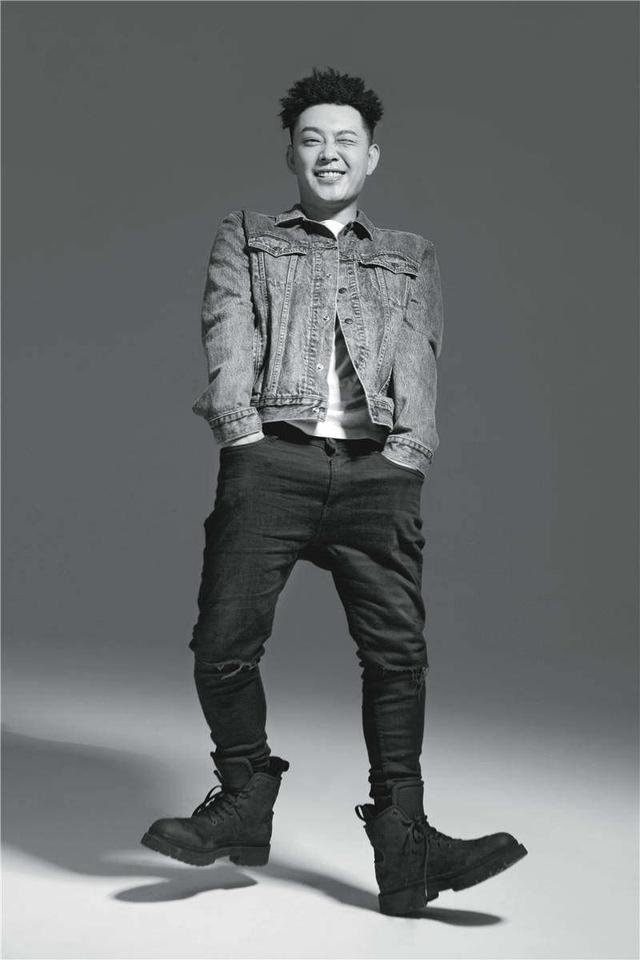





评论0